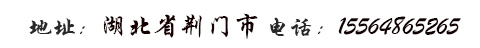昆明:我的无知游历
|
昆明:我的无知游历
早上七点的青年路还下着小雨,龙泉路上车辆照常拥挤,雨刮器在车前一来一回像慢播的电影。路过小菜园立交桥太阳出来了,未干的路面泛出明亮的色泽,细叶榕浓密地青翠,电动车在身旁匆匆轧过带起串串水珠,清脆有声。八月的昆明适合散步,如果你在,我们可以一起四处走走。顺着一二一大街走到建设路的路口,空气开始变得清新欢悦起来,路口向南去往滇池,向北可达世博园和金殿,向西是去往西站和筇竹寺的方向,向东则是翠湖和省图书馆。 去年的七月,那时我走过这个路口,写过一篇日记,一年转眼就过去了,而对于昆明两年很快也过去了。说起西站和筇竹寺,看过于坚先生写的《老昆明:金马碧鸡》我特意去过一次,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对于昆明的陌生和无知,就像我对它的许多其他部分一样,以前却是未知。上学期,和兵兵去筇竹寺,在西站附近我们寻着去往筇竹寺的公车,在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交接处茫然徘徊,好像还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时,我给走在铁轨上的他拍了许多照片,铁轨——浪漫而血腥的物件,谁还记得当年倒在滇缅铁路上的十万人?新闻说平均每隔八米就会有一架尸骨。这条滇缅旧道长长地绵延着,兵兵在铁轨上伸开双臂,像鸟儿一般轻盈,我在本子写着“人生或许也这般轻盈地卧在这条铁轨上无知地游历,单轨或是双行……”此时,我的身后是师大的本部即西南联大的旧址,它的对面是云大,再下去是民大的莲花校区。 在街边走着走着,我不由地给老师打了一通电话,问她可有时间一起出来看电影。听到我说只有我们两人,老师笑称浪漫。而这样的浪漫,我想或许也连接着许多记忆中的铁轨。中午的正义坊洒满了阳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在我心里都美仑美奂,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我来回地走了几遍。那些高高的梧桐树,让我想起法国文学,也让我忆起广州的西关和北京路。在披萨店里,我给老师看了几本我从省图借回来的书。聊起《大亨小传》,我们都觉得这个时代跟爵士乐的时代有点相像。盖茨比虽已死去多年,但说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总觉得有点像那时的美国梦:那个挥金如土的年代像被注入一剂毒药似的,疯狂,乐天,享受,富人们高高在上,许多颗跟里茨饭店一样大的钻石迷乱着众人的眼目,人们在音乐声中纸醉金迷,放肆地舞蹈。接着,我们聊起陈丹青先生的《无知的游历》。陈先生的书我都会读一读,与他以往的几本不同,这本书不厚,文字在八万字左右,伴以游历的图片,读起来很快。此书之所以称为无知的游历,陈先生说是因为他新到一国使其油然动衷的一刻,正是无知。而他的老师木心先生上文学课的时候,时常告诫学生走访各国的时候,必要熟读该国的人物与史迹,有备而去,才是幸福的出游。自然这“无知”是先生的谦辞。我常跟很多人说陈先生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启蒙老师,这是确凿的。因为读了他的书,我的阅读世界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门窗。因为读了他早前写的《多余的素材》、《退步集》,我找了《杜尚访谈录》及约翰·伯格等人的书来读,后者对于毕加索的议论至今以为经典。随着对图画艺术的兴趣渐浓,我对摄影方面的书籍也产生了兴趣,先是找了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后来又找了罗兰·巴特的《明室》,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来看,围绕着绘画和摄影的区别优异,我看到了不少精彩有趣的评论,也知道了一些著名的摄影师,如大家所耳熟的拍摄了《战士之死》的罗伯特·卡帕,在年2月拍摄《枪毙越共》的那一瞬间的摄影师埃迪·亚当斯。这些都是我在大二看他的书的时候从旁涉猎的。照相机一路发展到电影的形成又是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在对摄影书籍涉猎的同时也翻阅了一二。此书的游历由三篇不同的游记组成,分别写到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匈牙利和德国的几个城市。陈先生在书中对俄国文学发表的一些看法和议论,使我印象深刻。翻阅图册,念起书中段落,我跟老师还大言不惭地说了下面一段: “粗略而言,绘画清晰,文字混沌。但左手可能就是右手的倒影,双手合十,上帝就会出现在头上穹顶的壁画里。他只是看着他的王国,至于这国究竟是天堂的极乐净土还是人间的芳馨,他都一并心领神会。绘画与文学都是时间的艺术,是对时间和事物的凝固,就像琥珀对于蚊蝇一样。细节是主要的!两者之中举手投足,低眉顾盼皆是情感的凝聚;对于读者,画的留白间隙,目光的停驻与在文学欣赏中读文的停顿亦是通感。尽管描写的方式不一,但两者都表现出同样地沉浸、浓郁、美满。细节即是眷恋,深爱及思考,以及思考之余的意外之象和欲言又止。伟大的画家作家他们都和上帝一样了然,面色平静,一笔一画,爱而不乱。无情?无情。爱?爱!他们学会了上帝的表情!” 对于文学与绘画,我那点浅薄的知识不知怎的竟大放厥词,而追溯其来源可能始于毕沙罗的一幅静物油画。后来,我断续地看了一些画家和博物馆的画册专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的波普艺术等草草地阅览了一遍,在读艺术史之前竟也模糊知道了一些流派和画家的作品。自此,我对十九世纪的画家及画作也产生了兴趣,喜爱上了梵高,莫奈,库尔贝,安格尔和修拉等人的画作。对于画家写的书,我看的不多,主要也是十九世纪的,其中包括夏加尔的《我的自传》,塞尚和梵高等人的一些书简。 在俄罗斯的游历中,陈先生依次拜访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他们四人的故居,在说及俄国文学时对他们四位也进行了重点阐述。对苏联与中国绘画史上的渊源,书中略有提及。对于阿赫玛托娃我不太清楚,印象中她总让我想起写《钟形罩》的普拉斯。在俄国画家中,列宾因《伏尔加纤夫》已为我们熟知,小学课本里就有关于他这幅画的选文。陈先生说:“列宾是个好人,在善与美之间无可奈何:瞧见美丽的意大利绘画,他衷心叹道,艺术就该服从艺术;在一件描绘俄罗斯穷村姑的三流作品前,他看了看,哭起来,说是最好的艺术,描绘人性。”这幅画列宾画于26到29岁之间,画末他将自己的签名谦卑地写在了河滩和沙砾之间。其他几位俄国画家不一一细数,列宾的作品现今主要藏于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和圣彼得堡的冬宫美术馆(前些日子友人凌即去过)。而说起列宾,就不能不说到他与托尔斯泰的关系,这是题外话。当福楼拜看到《战争与和平》的法文初版,读罢第一册随即叹道:“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陈先生在说到列宾和苏里科夫的画时,仿照此句也说了一句,他们是文学家,文学家,一流的文学家,内里奥秘颇值得寻味。喜欢外国文学的人或许在心里都会给俄国文学留下一片广阔的天地,说起俄国文学可能还会激动地滔滔不绝。我最先看到别人盛赞俄国文学是在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上看到的,那时已经断续地读了一点俄国文学。 在这本书上,我涂画笔记最多的是普希金。圣彼得堡俄罗斯美术馆广场现今耸立着普希金的铜像,画面中他伸展的右臂落满了白鸽,目光看向远方,潇洒超然,看了不禁使人动容。在陈先生看来,他的超然激越是俄罗斯文学的异数,但“俄国文学却从普希金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读普希金的诗,一股子金贵的少年气。”普希金的诗也伴随了我高中生涯的开启,作为青春扉页的浪漫序曲,想起他的诗我会情不自禁地忆起自己的青春年华,或许很多人也是这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长大的我们,懂得了太多快乐的秘密!忘不了他的皇村回忆,也忘不了他无数的情简。老师曾对我说一个人到底爱过多少人才会懂得什么是爱。此刻,如果普希金站在我的面前,我也想问他一句,莱蒙托夫也是。他们二人有太多的相似,如同他们的作品《叶普盖尼·奥涅金》与《当代英雄》之间的雷同互文。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里写了几个深爱毕巧林的女人,而爱毕巧林我想就是爱他本人,我不禁臆测: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个人悲剧反映的可能是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不幸,总觉得文中有些地方是苦泪的,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反差,小说中的被爱可能是现实中的无爱,单方面的爱。老师告诉我,这在符号学中称为符号在场,意即指称对象不在场或缺失。 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未免自己成为话痨,在此略去不谈,文中有一段话谈及二人,可记于此处:“我不曾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谈论托尔斯泰,但《安娜·卡列宁娜》出版后,他那么骄傲地朝向欧洲,说,没有一部欧洲的小说能够与之媲美。他比托尔斯泰早逝近三十年;托尔斯泰谈及他,似不像对屠格涅夫及其他同行那么肆无忌惮:他曾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视技巧,作品粗糙堆砌;晚岁,忽又不安地看重这位年长几岁的同行,含着泪,讲了几句老年人才会说出的话,说是早该找他。他俩有过通问的记载吗?据说他出走前,桌面摊开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王不见王,这是中国的说法,照高尔基的意思,上帝与托尔斯泰是一个洞中两只熊,不好相处,其实另一只熊,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迟暮之年的托翁,在列宾的画笔下终于软了下去,高大、深沉而智慧的他也终于变回了一个迷惘的老头。去年看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对于他的出走我多了一层理解,但许多地方至今仍想不明白。老师印象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她说一个作者拜访托翁,看见清晨穿着睡衣漫步海边的托翁背影,那人惊叹自己遇见了上帝。想想,或许是该阅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了。跟老师聊起他们,我还说起了我喜欢的茨威格,他也写过拿破仑的战争,写过托尔斯泰的墓地,这些我都还记得,但对他写人时的“煽情”,我还保留着自己的那点脾气,老师也心有戚戚。 八月,八点黑的昆明夜色温柔。看完电影,吃过晚餐,便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地铁上我一路瞌睡,像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一天和夜晚,搜索记忆,为了我的无措,把它记在这里兴许也是必要的吧。 北京医院治疗白癜风费用北京最大白癜风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unmingzx.com/kmfz/70265.html
- 上一篇文章: 昆明一5岁男童下体严重烫伤脑死亡 疑遭“
- 下一篇文章: 昆明:立体停车场成“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