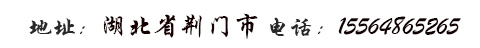曾出现在达芬奇手稿中的桥,却独在闽浙山
|
编木拱桥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建筑文明和历史时期,并不是中国独创。但这种桥梁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国性,因为他国的个案,其实都是灵光一现的“实验”甚至“游戏”,在历史中短暂出现,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只有在中国,尤其是闽浙山区,编木拱桥才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技术,并留下了数百年传承 廊桥的横梁上仍然留有前人墨迹(3月21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昊泽摄 编木拱桥是一种用木材交织起拱的结构形式“编织”而成的桥。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奇特、罕见的桥梁形式,编木拱桥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都非常少见。尽管特异,它还是被广泛地记载,出现在不同的建筑文明和历史时期:古罗马时期的恺撒大帝修建过,《清明上河图》里绘制过,达·芬奇也留下了类似的设计手稿,偷渡美国的日本船匠建造过,德国的园林和挪威的山中也曾出现过……结构巧妙独特的编木拱桥,在各个文化语境中都被视为独创或特例,更以“普适的独特性”一鸣惊人,成为一把理解人类建筑文明的钥匙。 清明上河图虹桥。(除署名外,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建筑历史学者刘妍历时十二载,涉猎多语种文献古籍,入深山渡重洋、挥斧子扛木头,踏访中外不同文化腹地遗存现场,穷极多种学术手段,去寻找编木拱桥的历史和故事。他的建筑史学专著《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从小切口深入到不同文明与文明的不同时期,勾勒出了“以构造思维为核心的人类历史地图”。这部特殊的技术史与社会史,让这罕见而非凡的桥梁建筑从历史中浮现出来,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建造历史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可以编织的桥梁” 展卷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东京汴梁城外汴水河上的一座拱形桥梁吸引了我们的视线。它与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编织”结合在一起,化直为曲,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架设在汴水河上。桥上人来人往,车马喧嚣,一幅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景象。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妍介绍,编木拱桥是我国传统木架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类,整个设计与构造极为特殊和精巧。所谓编木拱桥,就是用木头,而不是砖石,来构建拱形结构。它将木材横纵交织,好像编竹筐的经纬交织,来形成拱形,既受弯,又部分遵循砖石拱中的传力机制。除了力学原理上特殊,编木拱桥的构造也很特殊:平直的木材,通过编织、交叉、叠压、互相咬合等方式形成拱形,并且在特别的节点联结,施工上颇有一番技巧。 刘妍在造桥工地加工构件。 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编木拱桥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刘妍介绍说,在有些文明中,我们只在史料里看到它来过世上的痕迹,现实中却不见其影。甚至连《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也是消失近千年的技艺,普通观者未必能注意到它的特殊之处。 事实上,《清明上河图》也有不同版本存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明清版本中,虹桥是石拱桥;而北京故宫藏的宋代版本中,细心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这座桥是用“编织”木材的方式形成的拱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种“筷子搭桥”游戏,和它的结构非常相似。但在宋代之后,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图像中,这种桥梁似乎都不见了踪影,甚至在学术史上,也被当作历史的孤例。 编木拱桥如此奇特,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只是画师自己虚幻的构想。但编木拱桥确曾在北宋出现过。刘妍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对它的描述。比如《东京梦华录》讲的就是东京汴梁城外的事,它说‘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宋会要》中说‘编木为之,钉贯其中’,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 刘妍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有学者在宋人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里也发现了另外一座小桥,虽然小巧,但是建造结构与汴水河上的这座编木拱桥是相似的。 江山秋色图虹桥。 虽然编木拱桥在世界文明史中“昙花一现”,但我国浙南闽北山区至今仍保存有大量、完整的编木拱桥桥梁群,自明末以来的各式木拱古廊桥就有多座,主要留存在福建省寿宁、屏南、周宁、政和、建瓯和浙江省庆元、景宁、泰顺等县市,分布在闽浙两省交界山区从南到北大约公里范围内的深山老林里。这些山区县乡至今还保留着匠作的传统,其中两个传承最久的“编织”造桥家族,至今已传承七八代,历时多年。 9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22座“闽浙木拱廊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闽浙两省七县(浙江泰顺、庆元、景宁,福建寿宁、周宁、屏南、政和)正积极抱团共同申遗。 “普适的独特性” 事实上,编木拱桥作为一种奇特、罕见的桥梁形式,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中都留下了平行且独立的“奇异共振”:除了北宋东京汴河上的国家工程和明清山民的创造,还有征讨日耳曼人的古罗马皇帝、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巨匠阿尔伯蒂、天才设计师达·芬奇以及19世纪的日本、德国和挪威木匠,他们在人类文明长河的不同角落,都或多或少创造出相似但又有着明显差异的编木拱桥。虽然我国的案例最为成熟和令人瞩目,但编木拱桥却并非我国独创或特有。 汉庭顿圆月桥。 “我硕士毕业后通过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接触到闽浙木拱桥,后来又到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建筑考古学,将这种桥梁作为博士研究课题。当时学者们普遍将这种桥梁视作一种‘中国类型’,除了中国案例外,只知道达·芬奇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我在博士研究过程中,挖掘到更多文明的案例,让我开始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寻宝之旅。”也因此,刘妍将博士论文选题调整为编木拱桥的世界史。 中国案例之外,最有名的编木拱桥设计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设计师达·芬奇。达·芬奇的存世手稿显示他甚至做过一批编木拱桥的设计图样。西方一些学者会用“达·芬奇桥”来指称这种桥梁设计,而达·芬奇的设计图比《清明上河图》晚了多年,所以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他是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影响。 达·芬奇的木拱桥设计。 刘妍为了弄明白达·芬奇的设计理念从何而来,专门“啃”了一阵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收集了达·芬奇的手稿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文献。“结果我发现,达·芬奇其实是在研究罗马的历史后受到了启发。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恺撒在征讨高卢地区时建造了一种军事桥梁,采用了一种类似编木的节点机制。达·芬奇就是从恺撒的莱茵桥得到启发,才发明了编木拱桥,与中国和东方的同类桥梁其实没有关系。” 刘妍告诉记者,他在读博期间就力图在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寻找收集类似的桥梁结构遗迹。他注意到美国学术机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Library)的日本园林中,有一座建造于上世纪初,由一位偷渡到美国的日本木匠建造的小桥,与《清明上河图》中的编木拱桥非常相似。“当时《清明上河图》还深藏在紫禁城中,绘画细节还不被外界所见,所以这座桥跟《清明上河图》肯定没有关系。它的技术源头就值得挖掘了。” 德国木工手册中的编木拱桥。 刘妍还在德国学习了木构匠作,他在一本出版于年的德语木工手册中找到了一座小桥,它出现于书中的园林建筑章节,桥跨度只有4米,叫作“所谓的高加索桥”。作为园林景观,这座桥有猎奇性质,但结构上也采用了编木拱桥的设计。年,在博士毕业后的北欧旅行中,刘妍又在当地文献中发现了一座挪威编木拱桥案例,它建于地广人稀的挪威中部山区,是十八十九世纪矿产开发热潮时的产物,目前仅以老照片形式存在于博物馆中。这几个案例都找不到任何和中国的直接联系,它们的出现都与本土传统和时代需求密切呼应,是在本地构造和发展起来的。 挪威历史照片中的编木拱桥。 刘妍认为,编木拱桥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罕见而非凡的桥梁结构形式,无论它们出现在何方,都被认为是不寻常的创造,甚至被当作独创。“它们以适切的姿态,平行且独立地出现在多个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从自己的文化土壤当中长出来的。它既是普遍的又是独特的。在这些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中,编木拱桥以‘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共性,成为建筑历史上一种无与伦比的现象。” 中国编木拱桥的技术逻辑与社会土壤 刘妍在对十多个国家的踏访和资料搜集中发现,编木拱桥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建筑文明和历史时期,并不是中国的独创。但另一方面,这种桥梁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国性,因为他国的个案,其实都是灵光一现的“实验”甚至“游戏”,作为设计者的思维游戏或园林小品,在历史当中短暂地出现,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只有在中国,尤其是闽浙山区,编木拱桥才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技术,并留下了数百年传承。 刘妍在对闽浙木拱桥进行测绘。 为什么唯有闽浙山区可以产生成熟的编木拱桥营造传统呢?刘妍从9年就开始进入闽浙山区做田野调研。作为一位建筑系毕业生,他决定把这多座历史遗存全部测绘一遍。而在十余年的勤勉调研和测绘之后,他发现要想真正理解建筑,必须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中。 通常认为编木拱桥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产物。确实,在亚洲,编木拱桥是桥梁技术的一个顶峰。但这种技术高峰,却扎根于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都不发达的闽浙偏远山区,在崇山峻岭的艰险环境中,山民们没有条件去营造“常规”的桥梁,才有动力去探索这种新奇形式的可能性。 闽浙木拱桥:后垄桥 刘妍解释说,闽浙交界山区的桥梁建设,常常会遇到类似悬崖上或深潭上建桥的险要环境。若想建造石拱桥,施工中需要宏大、完善的脚手架,人工和经济上的压力负担很大。而在这里发展出来的编木拱桥,可以巧妙地使用简单乃至简陋的脚手架来施工,节约了相当多的资源和人力投入。而木拱桥的发展不仅是在材料上将小石块变成了长长的木梁,而是配套了一整套榫卯结构设计。施工中,脚手架的布置也非常关键,高空作业更是惊险,是桥匠家族的核心技能。这些技能能够被山民们创造出来,又得益于当地在历史上动乱年代留下的习武传统及水上作业能力。这些不同的历史因素,像齿轮一样咬合作用,推动了闽浙木拱桥走向技术成熟。“所以,中国山区的编木拱桥,是在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夹缝中,被‘逼’出来的技术。”刘妍说。 木拱桥发展出的榫卯系统。 从历史视角来看,某种技术或制式的流行或衰落,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分工及匠人家族的命运起伏深刻勾连。在闽浙地区,编木拱桥在特殊的社会需求土壤中被孕育,在地区经济的发展、交通“刚需”之下,演化成一整套高效有序、构造与施工相配合的技术体系,形成了超过年的匠作传承。而建造编木拱桥的“匠人家族”,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地位呈现出一种“跷跷板”式的特性:地域发展得越好,家族条件越好,造桥技术反而不太容易产生;恰恰是位置更偏远、经济条件更差的地方,地位边缘低下的匠人中,才“逼”出了更娴熟的造桥技术。 模型示意:在惊险的环境中建造编木拱桥 在技术与科学已然大发展的新时代,“编木拱桥”进入“非遗”名录,保存和挖掘古代技术并将之流传下去,到底有怎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于怀旧精神还是科学技术?刘妍的专著《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出版后,也引发了这样的讨论。 刘妍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科学精神背后蕴含着的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通往宇宙星河。我们要走上这条“高速公路”,但也不应贬低和抛弃那些“山间小路”,它们同样蕴含着许多美妙的风景和奇妙的经历,丰富着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即使站在“科学中心主义”的视角,那些所谓过去的、落后的甚至“低级”的技术文化,同样也可能是我们今天技术文明的“生态”保障或“基因池”。就像编木拱桥的技术形式也出现在“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建筑大师王澍的作品中,为我们的民族科技贡献了异彩。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unmingzx.com/kmly/84267.html
- 上一篇文章: 李元芳的云南高校种草指南农大昆院津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