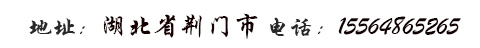苏家村采访笔记远去的村庄
|
去采访摄影三兄弟。原想这个故事的指向肯定是个人突破阶级局限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但聊下来竟然指向更广阔的时代变化。 虽然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强烈的人类自觉,但他们也算是被命运选中的,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苏家村,嵩明县城南边的多人口汉族村。附近有中国西南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还有一个因时代与省会波动而出现的旧货交易市场——昆明城大拆大建,拆下来的旧建材都运到这里交易。 问在苏家村娶妻生子过日子的李家老三,60几岁的李克文,家门前排了两公里的旧钢筋、角铁都是怎么来的,他说:“门前空着么,他们就在这边卖了。” 兄弟仨都是农民,年轻时干极重的体力活,曾经一天一夜地挑磷矿,装满60吨的火车货箱。 现在都不种地了,收租为生。三哥自建房一层出租给旧货商(本条街家家如此),每年收租几万;田地数亩出租给外来户种大棚蔬菜。还承包了亩山地雇人种板栗。 嵩明,历史上的诸葛亮与孟获的结盟地(传说,地域上近曲靖,那里是七擒孟获地),虽然离昆明主城60公里,但省会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会波及该县。 从北京朝阳区到昆明当市委书记的程连元马上到嵩明视察——这是他接任滇中新区党工委书记兼新区主任后首次到该管辖地,当地政府部门为此忙得脚打后脑勺:为了做展示工作效能的展板,有人加班到半夜12点。 苏家村房屋密集,村路灰土覆盖,偶尔闪出块田,撂着卷成捆的稻草,半黄半绿。一眼望出种了啥的裸田在嵩明已不多见——昆曲高速直达嵩明,处于昆明和曲靖两大城市之间的小县城是云南为数不多的平坝所在,取代从前呈贡(从前的县,现在的区,昆明卫星城,市政府新办公地,未来出省的高铁站也在那里),成为供给昆明和周边乃至外省蔬菜的大棚种植地。 头天村里有人过世,办白事使用了公共集会地,导致老人聚会挪到第2天:唱歌、耍龙、拍集体照个人照、杀猪、百人大聚餐。 李家老三连续几年都把养在数公里外承包地的肥猪贡献1口,给聚会餐做主菜。钱也捐上元。他的名字被写在红榜首名。 “我弟是入赘的。以前家里穷,房子不够分。入赘你懂么?”李家老大问。 昨日还是另番布置的村集会大院现在欢声笑语。二层小楼的一层大厅摆满圆桌木椅。百多人分成十几桌。菜用碗盛,由帮厨男女以托盘一次上齐:豆腐圆子、莲藕炖排骨、山药红萝卜炖排骨、红烧猪皮、炸春卷、韭菜鲜肉饺子、苦菜汤、白肉猪肝凉拼、烤酥鸭、凉鸡、小炒肉、凉米线。 村长着笔挺蓝西装,衬衫雪白,头发吹得光光的。 席间穿红着绿的女子不时闪眼往坐着外来户(吾们)的桌上看。 “那个,戴皮帽子的,90岁啦!”李家大哥指给我看。“那个,80多!” 拍百人合照时我想借机摆置下,搞张三兄弟拿相机蹲在诸老人前面的大排场图片——老四想照办,招呼大哥,刚作势要站过去,即被三哥制止:“不能!” 我赶紧作罢。心想怕是村里自有秩序。 老人解散,老三媳妇上前笑着:“他们不是我们苏家村的,他们是杨桥的。” 大哥和四弟弟不是村里人。尽管各自宅院离此地也就是几步路。 吃饭了。桌上开始让菜,你夹给我,我夹给你,行必要礼数。 大哥说: “我们这儿,办好事家家出来帮忙。家族越大来帮的人越多。有的老板常年在外,别人家办事,他也不回来,也不出人帮忙。到他家有事,没人去,请人要花钱。” “我们家没有人当官。但我们家在杨桥李家里,是人最多的。” 尽管村庄里很多人都不在种地,但乡俗村序依旧发挥作用。村民通过聚会、仪式(舞龙)凝聚人心(只限老人和留守者),通过助他和得助彰显存在价值。同时,他们也正在经历从农耕社会向市民阶层过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如村民口中的“老板”般外出就业,丧失与村里在人际上的紧密关联,靠雇佣来完成传统仪式——生老病死、红白喜事。 最终,他们将再不回头地走向城市,淹没在更急速的时代洪流中。 苏家村女子舞龙队 乡间做半旦。往往是每年9月到第二年清明节前。这是农耕社会的习惯,秋收开始到春种之前各家各户出门组织友邻聚会吃喝,联络感情,凝聚人心。 乡厨出品。云南汉族村庄,聚会习惯吃杀猪菜:不是专门的厨师做的,谁家办席,由各家出志愿者组成厨房团队,沿袭乡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在福建、台湾,乡厨是专业的,在乡间接到订单就带队带工具前去组织,搭炉灶,出大菜……第一代乡厨后来成长为都市豪华酒店的顶级大厨和餐饮界大佬。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unmingzx.com/kmwh/83830.html
- 上一篇文章: 警惕针对学生群体实施的电诈犯罪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